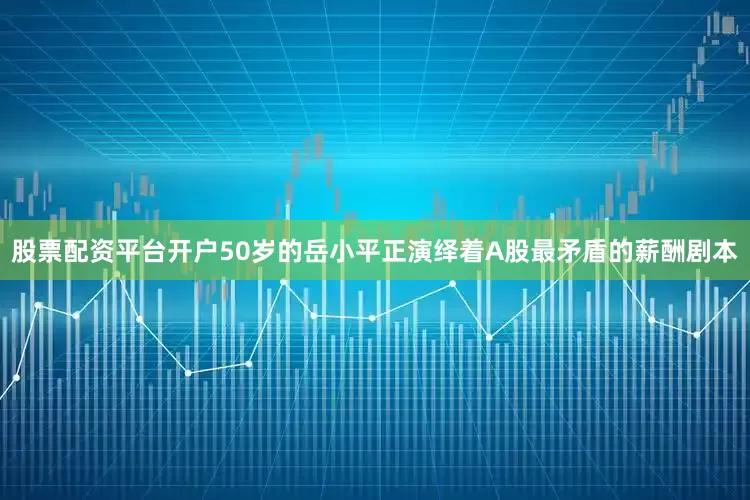在《红楼梦》第八回“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”中,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情节:“一语未了,忽听外面人说:‘林姑娘来了。’话犹未了,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,一见了宝玉,便笑道:‘嗳呦,我来的不巧了!’”①

上述情节承接贾宝玉、薛宝钗的“金玉既合”,无论是小说情节的转折,还是林黛玉形象的刻画,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同时,本段也是《红楼梦》文本校勘中较为重要的一例,其原因在于“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”一句,在《红楼梦》的不同传本中,文字亦有细微差别,试举数例如下:
话犹未了,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。(甲戌本)
话犹未了,林黛玉已走了进来。(戚序本)
话犹未了,林黛玉已摇摇摆摆的来了。(程甲本)
话犹未了,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。(程乙本)
仅就本句的校勘而言,如果不考虑戚序本近于“质木无文”的描写以及不同脂本间细微的异文,以甲戌本为代表的脂本和程本之间的本质差异,在于对林黛玉步态“摇摇”或“摇摇摆摆”的描写。
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,学界几乎公认以“摇摇”为佳,而以“摇摇摆摆”为程本对原著文字的篡改。
问题在于,何谓“摇摇”、何谓“摇摇摆摆”?“摇摇摆摆”真的是如此严重的败笔吗?这一细节几乎从未得到学界的正面关注和专门讨论。
对此,本文将首先回顾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历程,在此基础上,结合具体语料进行讨论。

1927年,胡适发现甲戌本,标志着《红楼梦》版本研究新时代的到来。次年,胡适在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一文中,以“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”专章比对了甲戌本和程本之间的部分文字异同。
针对《红楼梦》第八回对林黛玉步态的描写,胡适指出:
原文“摇摇的”是形容黛玉的瘦弱病躯。戚本删了这三字,已是不该的了。高鹗竟改为“摇摇摆摆的”,这竟是形容詹光、单聘仁的丑态了,未免太唐突林妹妹了!”②
事实上,早在胡适撰文的十余年前,上海有正书局以戚序本为底本石印出版《原本石头记》,即以眉批形式,收录民国学者狄葆贤(平子)的评点。

在本回中,狄葆贤指出:“‘林黛玉已走了进来’句,今本改为‘已摇摇摆摆的来了’。‘摇摇摆摆’字样,描写薛(璠)[蟠]、贾环等人则可,今本以之唐突潇湘也!”③
在有正书局本的时代,学界尚未意识到脂本系统的存在,狄葆贤也未见“摇摇的走了进来”作为另一种校勘上的可能,仅在有无“摇摇摆摆的”五字之间,狄葆贤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五字的不妥。
“摇摇”优于“摇摇摆摆”,一经胡适判定高下,遂成为学界共识。
1950年,俞平伯《红楼梦脂本(甲戌)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》一文,在狄葆贤“唐突潇湘”观点的基础上指出:“我想这大概近乎原本。‘摇摇’自可,下加‘摆摆’,即成恶礼矣。”④
尽管胡适和俞平伯一致认为“摇摇”二字为上,但二者对“摇摇”的理解却不尽相同。具体而言,胡适强调“摇摇的”步态更符合林黛玉的“瘦弱病躯”,着重考虑林黛玉的身体状态;而俞平伯则强调“摇摇摆摆”的步态近乎“恶礼”,偏重从礼法规矩层面的考量。
时至今日,涉及这一问题时,研究者几乎都在沿袭胡适、俞平伯的观点。其中,不乏承袭胡适“瘦弱病躯说”者,如邹光椿认为“‘摇摇的’是形容黛玉的瘦弱病躯”⑤、王漫宇认为“使人好像看到她弱不禁风而又不失轻盈敏捷的神态。”⑥
亦有论者沿袭俞平伯从礼法规矩角度的判断,如周中明认为“摇摇摆摆”一词“使林黛玉猝然成了一个风骚浪荡的泼妇形象”⑦,何满子认为“林姑娘这样的闺秀是不会也不该‘摇摇摆摆’的”⑧,格非认为“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竟然有了大腹便便的轻浮之态”⑨,梁归智则认为“让绝代佳人鹅行鸭步,岂不贻笑大方” ⑩,等等。
此外,还有学者从新的角度佐证“摇摇”二字的合理性,例如胡文彬《微步动瑶英——林黛玉的“走”态》,提出“摇摇”二字与古代妇女佩戴的步摇装饰有关——“原来林黛玉的‘摇摇’是指她走路时‘高髻’上的簪钗下垂饰物——‘垂珠’在‘摇’动,以此来形容女孩走路姿态之美。”⑪

另一方面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,有部分学者从社会生活史角度,将“摇摇摆摆”的步态作为考察缠足风气的社会风俗史料——“分明是由于金莲三寸,绣鞋一双,袅娜轻盈,临风依依”⑫、“只能凌波碎步,摇摇摆摆,行动如弱柳扶风。于是,林黛玉式的美人形象就算完成了”⑬。
但问题在于,《红楼梦》中女性是否缠足、曹雪芹是否有意识地强调女性缠足的特征,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达成统一意见;另外,曹雪芹在本回暗示林黛玉缠足的必要性尚可商榷。
因此,“缠足说”似不能作为“摇摇摆摆”在文字上取胜的论据,既没有成为学界的主导意见,也未曾动摇过胡适以来的主流看法。
综上所述,从胡适的“瘦弱病躯说”,到俞平伯的“即成恶礼说”,甚至包括当代学者提出的“步摇说”,“摇摇”优于“摇摇摆摆”,已基本成为现代《红楼梦》研究者的共识。

如果说,学界普遍认识到“摇摇”在文字上优于“摇摇摆摆”,始于上世纪20年代胡适发现甲戌本,那么,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是:自清乾隆五十六年(1791)程甲本《红楼梦》刊行,直至发现甲戌本的一百余年间,众多读者、评点者在没有他本可资参校的情况下,是否曾意识到程本系统“摇摇摆摆”用词的不妥呢?
事实上,如果将考察范围集中在清代中后期《红楼梦》的主流评点者,即,从东观阁本到桐花凤阁评本,从“三家评本”到“八家评本”,在这些占据主流地位的评点本中,评点家们无一对“摇摇摆摆”的描写提出过指摘。
在针对“摇摇摆摆”一句的评点中,东观阁本评点:“黛玉出话刺人,本非福相”⑭,张新之评点“金玉既合,此人便到,乃大章法”⑮,姚燮评点“何等尖毒”、“何等敏捷”⑯。
上述评点,或针对林黛玉的话语内容,或重在提示林黛玉的语言风格,或以文章学的评点思路讨论小说章法,却皆未对“摇摇摆摆”一词提出质疑,这本身就体现了默许甚至肯定的态度。
值得关注的是民国学者王伯沆的评点。针对“林黛玉已摇摇摆摆的来了”一句,王伯沆绿笔评点“婉若游龙”⑰。这是一处极为重要的评点,其意义体现在:
首先,王伯沆直接肯定了林黛玉“摇摇摆摆”的步态描写,并留下“婉若游龙”的评语,这无疑是对“摇摇摆摆”一句的较高评价。
其次,王伯沆绿笔评点的时间集中在1921-1922年间⑱,此时距离胡适发现甲戌本不过几年之久,这至少证明了,在胡适以“摇摇”校勘“摇摇摆摆”的前夕,仍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评点者对“摇摇摆摆”持肯定态度。

再次,王伯沆的评点时间下限已至1938年,“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,他最早将脂本系统的版本和程本系统的版本进行全面、细致的校勘,并作了详细的记录,间有分析评述。”⑲在这样的情况下,王伯沆仍未对“摇摇摆摆”提出校改,这无疑从客观上反映了王伯沆本人的倾向。
由此可见,自《红楼梦》程甲本问世,到脂本系统被发现和利用的百余年间,在占据主流地位的《红楼梦》评点中,“摇摇摆摆”并没有引起明确的指摘,这一倾向在1928年后发生了明显变化,这不得不说是《红楼梦》的校勘和评论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。
正如前文所述,以1928年胡适发表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为标志,学界对程本系统“摇摇摆摆”一词的评价发生了整体性的转变。

但是,在面对“摇摇”与“摇摇摆摆”二者孰为高下的问题时,不仅要求读者依照当代人的语言习惯,更应该将《红楼梦》放在其产生时代的语境中。
换言之,“摇摇”的具体词义是什么?当曹雪芹用“摇摇”形容林黛玉的步态时,是出于何种考虑?而后人在将“摇摇”改为“摇摇摆摆”时,又基于何种出发点?为了解决上述问题,需要结合具体文献语料进行细致分析。
如果排除“摇摇”一词的动词词性(如“摇摇手”、“摇摇头”等),《汉语大词典》对“摇摇”的解释如下:心神不定貌;摆动、摇曳貌;远貌。以上基本概括了“摇摇”一词的主要形容词义项。那么,对于作者而言,更偏重哪一种用法呢?
笔者认为,“心神不定貌”固然可以勉强说通,但却不甚符合“摇摇”的基本用法和上下文语境。
首先,这是一个高度书面化的典故,今考《诗经·黍离》:“行迈靡靡,中心摇摇。”毛传:“摇摇,无忧所愬。”⑳又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:“寡人卧不安席,食不甘味,心摇揺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。”21
在后世文学创作中,这一典故往往用以描摹人物的心理状态,例如《萤窗异草》中《无常鬼》《姜千里》两篇,先后出现“此子之心,尚摇摇如悬旌也”“人心惶惑,摇摇如悬旌”22。
其次,即便将“心神不定貌”直接用以修饰人物动作,仍与林黛玉此时对薛宝钗的态度不符。
在小说第五回,固然已交代了林黛玉“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”23,但在第八回时,“金玉良缘”之说尚未公开化,即便是贾宝玉,此刻也刚刚被莺儿点醒,林黛玉更是无从知晓。林黛玉纵然有所谓的“尖毒”(姚燮评点)之语,表面上仍是戏谑、打趣的,远没有达到“心神不定”的程度。

再次,根据上下文,林黛玉此时并不知道贾宝玉已在梨香院,前往梨香院的目的只是探望薛宝钗,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因贾宝玉在梨香院而心神不定。因此,《红楼梦》描写林黛玉“摇摇的走了进来”,并非偏重于“心神不定”义项。
同样,“远貌”义项亦与小说前后文意不符。姑且不论自宋元以降,通俗文学中表述距离遥远往往习惯用“遥遥”而非“摇摇”,仅从梨香院的地理空间即可排除这一义项。根据小说叙述,梨香院作为“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”24,后来曾入住十二个小戏子,其占地空间不会很大,何况薛宝钗的居室只是其中一间。
当林黛玉进来时,外面人通报“一语未了”,林黛玉已走了进来,足见居室的狭小。因此,林黛玉的出现不可能有“由远及近”的效果,“远貌”义项也基本可以排除。
由此,“摆动、摇曳貌”义项很可能最接近作者写作的初衷——林黛玉以摆动、摇曳的步态,走进了薛宝钗的居室。“摇摇”一词使林黛玉摇曳生姿的步态跃然纸上,既凸显了林黛玉的优雅气质,又令人联想到林黛玉的体弱多病和孤高自许,自然是成功之笔。

甲戌本、己卯本 “摇摇”句皆有侧批“此处画出身”25 26,显然是对这一描写的肯定;民国以来,胡适的“瘦弱病躯说”、俞平伯的“礼法规矩说”、现代学者的“步摇说”,在各有侧重的同时,皆本源于这一义项。
然而,必须指出的是,“摇摇”的步态或许暗合林黛玉的“瘦弱病躯”、“礼法规矩”,但这只是读者的间接联想,“摇摇”一词本身既没有与“瘦弱病躯”的逻辑关联,又没有与“礼法规矩”的内在联系。
事实上,“摇摇”一词的修饰对象非常宽泛,在唐宋以降的正统文学创作中,“摇摇”作为“摇曳、摆动貌”大量出现,既可以形容灿烂的春华(宋谢翱《雨后海棠》“春光揺揺一万里”27),也可以描写繁茂的秋实(宋丁谓《梨》:“摇摇繁实弄秋光”28);既可以衬托朴素无华的气质(清曹烨《李圣生斋中梨花盛开》“素影摇摇曳缟裙”29),也可以寄托孤单落寞的情感(清高士奇《放鸢行》“摇摇渐觉孤影细”30)。
随着大量前人创作的积累,在《红楼梦》产生时代的语境中,“摇摇”作为“摇曳、摆动貌”,已在文学史上形成特定意象和相对固定的用法。
由此引申,在古代诗歌创作对“摇摇”一词的使用中,用“摇摇”形容柳树是一种常见的修辞习惯,这或许由于柳树枝条修长、容易随风起舞,或许柳树在文学创作中常与离别、乃至悠长思绪相结合。
例如,唐杜牧诗“揺揺远堤柳”31、唐温庭筠诗“摇摇弱柳黄鹂啼”32、宋陆游诗“湖上新春柳,揺揺欲唤人”33、清樊增祥诗“溪柳揺揺绿可怜”34,等等。作者是否有意以“摇摇”暗合林黛玉的“弱柳扶风”之态,是大可见仁见智的。

如果上述分析成立,那么,当曹雪芹用“摇摇的走了进来”形容林黛玉的步态时,无疑是将一个古雅的修辞习惯纳入《红楼梦》的文本之中。
作者对“摇摇”一词的使用,便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的“瘦弱病躯”、“礼法规矩”的考量,而在实质上是将文学史上既有的、水木光华的“摇摇”风姿,与林黛玉的优雅步态构成互文关系,这是曹雪芹赋予林黛玉的独特气质。
正因如此,脂批“此处画出身”,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“摇摇”步态和林黛玉大家闺秀出身的表面联系——事实上,全书中多有比本句更为经典的、刻画林黛玉才貌学识的段落——更重要的是,作者通过学识积累和匠心独具,将林黛玉的形象植根于深厚的文学传统之中,从而使一个古雅的修辞习惯在文本中得到重现,行之有效地拓展了小说文本的意义空间,这才是“摇摇”与林黛玉“出身”的深层联系。

尽管曹雪芹在使用“摇摇”一词时,体现出独特的匠心,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,在既有的文学创作中,“摇摇”作为“摇曳、摆动貌”,其修饰对象在特征属性上更偏重于物态——例如,形容悬垂之物被风吹动(如唐白居易《长恨歌》:“翠华摇摇行复止”35)、植物随风摆动(如宋陆游《中庭纳凉》:“摇摇楸线风初紧”36)、水波摇荡(如唐孙鲂《杨柳枝》:“入流穿槛绿摇摇”37)、灯火摇动(如金元好问《赠答张教授仲文》:“秋灯揺揺风拂席”38)等等,却极少有直接以“摇摇”修饰人物的先例。(在文学史上,虽有唐人《会仙诗》“彩凤摇摇下翠微”39,但“摇摇”的主语毕竟是“彩凤”而不是“仙人”)。
在人物描写中,“摇摇”常用以描写人物衣饰,但其中心语往往被明确为特定衣饰、而不是整个人物。
在诗文创作中是如此,如唐张祜《咏风》以“揺摇歌扇举”40描写扇子、宋欧阳修《送王平甫下第》以“归袂揺揺心浩然”41描写衣袖、宋陈普《莲花赋》以“灿灿琼台,摇摇玉珮”42描写首饰,等等;在小说创作中亦是如此,如《太平广记·柳氏传》描写柳氏“轻袖摇摇,香车辚辚”43、又《夷坚甲志》卷四《吴小员外》描写当垆女“幂首摇摇而前”44,二者都明确了“摇摇”修饰的中心语是“衣袖”、“幂首”,而不是“柳氏”和“当垆女”。
在明清通俗小说、戏曲中,甚至很少有用“摇摇的”直接形容人物动作的语料。由此引申,以“步摇说”阐释“摇摇”,似需进一步文献语料支持。可见“摇摇”一词看似信手拈来,却堪称曹雪芹的创新之笔。
由此不难理解,这一创新之笔固然取得了精妙的文学效果,但它不同于既有的修辞范式,也不符合当时人的语言习惯。

这就势必造成同时代读者接受上的隔膜。尽管已有学者指出,早在程本问世之前,甲辰本和舒序本中已出现“摇摇摆摆”的说法,程本的改动未必无据45,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——无论这一“修改者”是甲辰本、舒序本的抄写者,抑或是程、高等人,该“修改者”在面对“摇摇”一词时,极有可能在强大的语言习惯下,仍将“摇摇”视为一个修饰物态、而非人物体态的词汇。
那么,“修改者”可能的做法无外乎两种:其一,直接删去这一状语(如戚序本未必是简单的文字脱漏);其二,加以改动,使之符合当下的语言习惯——这或许正是林黛玉“摇摇摆摆”步态的成因。
正如上文所述,如果某一清代中期的“修改者”在语言习惯的驱使下,以“摇摇摆摆”取代“摇摇”,由此引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,这一改动真的是如此严重的败笔吗?

从常理推测,这一“修改者”无论文化水平如何,对“摇摇摆摆”这一基础词汇和《红楼梦》人物的褒贬立场应有基本掌握。如果“摇摇摆摆”一词如此不堪入目,“修改者”如此“丑化”林黛玉的出发点又何在呢?
为了解决上述问题,就需要对“摇摇摆摆”一词的适用范围进行归纳。不同于“摇摇”作为“摇曳、摆动貌”,在修饰对象的特征属性上偏重于物态,“摇摇摆摆”的诸义项在修饰对象的属性上历来包括人物。
同时,相较于源自《诗经》《汉书》的“摇摇”典故,“摇摇摆摆”的口语化色彩更为浓厚,常见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之中——这些通俗文学文本,直接构建了“修改者”所处的语言环境。
因此,有必要考虑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学创作中,“摇摇摆摆”的具体修饰对象,换言之,在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,都有哪些人物,曾以“摇摇摆摆”的步态出现?
自明代以降,直到程甲本《红楼梦》问世之前,在小说作品中,“摇摇摆摆”的具体修饰对象既有市井无赖(如《水浒传》中西门庆“自摇摇摆摆,踏着八字脚去了”46),也有鲁莽粗汉(如《西游记》中猪八戒“摇摇摆摆,对高老唱个喏”47),既有草莽英雄(如《水浒传》中李逵“去了双斧,摇摇摆摆,直至堂前”48),也有三姑六婆(如《拍案惊奇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》中赵尼姑“摇摇摆摆,同春花飞也似来了”49);甚至还被用以讽刺故作斯文的文人丑态——“书案上摇摇摆摆,酒席间闹闹垓垓”50。
正是由于这些作品和人物形象深入人心,才给民国以降、乃至现代学者留下“描写薛蟠、贾环等人则可”(有正书局本眉批)、“大腹便便的商人和拈字作酸的措大才摇摇摆摆”51的印象。

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“摇摇摆摆”的修饰对象被严格限定为负面人物,也并不意味着“摇摇摆摆”天然地带有贬义色彩。事实上,“摇摇摆摆”一词的适用范围非常宽泛,例如:
其一、形容人物泰然自若。
如《拍案惊奇·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》中,“只见张果摇摇摆摆走将来,……雪白一口好牙齿,比少年的还好看些。”52此外,也多用于描写人物通过乔装变化后坦然的神态,如《水浒传》中,吴用和李逵为了“智赚玉麒麟”,乔装打扮后,“摇摇摆摆,却好来到城门下”53,又如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第二十九回,碧峰长老先后三次“摇摇摆摆”进入羊角洞,54等等。
其二、形容人物步态不稳。
如《二刻拍案惊奇·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》描写李御史出场:“船舱门开处,摇摇摆摆,踱上个御史来。”55
其三、形容人物行为体面。
如《三刻拍案惊奇·冤家原自结 儿女债须还》中,吴婆夸赞徐英“你看他在街上走,摇摇摆摆,好个模样。”56《再生缘》第六十九回:“看姑娘,摇摇摆摆多体面,母亲何不学她身?”57

其四、形容妇女步态优美。
如《水浒传》描写潘巧云出场:“布帘起处,摇摇摆摆走出那个妇人来。”58《拍案惊奇·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》描写小娘子出场:“那小娘子乔妆了……摇摇摆摆,走到园亭上来。”59
就褒贬色彩而言,上述诸例无疑具有中性、甚至偏向褒义的色彩。就修饰对象而言,例一、例二或为仙人张果老,或为“智多星”吴用,或为“祛蠹除奸、雷厉风行”60的李御史,此外,还有《红楼梦》第一一七回,描写“那和尚便摇摇摆摆的进去”61;成书稍晚于程甲本的《续红楼梦》第七卷、第十五卷,先后两次描写贾宝玉“摇摇摆摆”的回来(或进来)62,这些无疑都是正面人物。
在文例中,固然出现荡妇潘巧云、“河南妓家”小娘子,但是,在二人出场时,在石秀和潘富翁看来,只知其为富户妻妾,而不知其为荡妇、妓女,不能笼统地加以贬抑。这似乎足以证明“摇摇摆摆”的适用范围远比今人想象中更为宽泛。
因此,在家喻户晓的《水浒传》、“三言二拍”等作品的影响下,在某位清中期“修改者”的语言习惯中,用相对通俗而常见的“摇摇摆摆”取代古雅的“摇摇”,无疑有助于消解接受上的隔膜感,使其更符合当下的语言习惯。
此外,值得一提的是,“摇摇摆摆”的姿态也与此时期妇女缠足风气有关,如对潘巧云,小说同回明确描写其“翘尖尖脚儿”,在清人俗曲中,还有将“款金莲,摇摇摆摆把牙床傍”63作为赏玩妇女姿容的细节。

用“摇摇摆摆”描写妇女缠足后的姿态,虽未必符合曹雪芹的本意,但对于“修改者”而言,却未尝不是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熟语。以上诸因素,或可为“摇摇摆摆”进入《红楼梦》文本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。
问题在于,为何“摇摇摆摆”一经胡适提出后,便受到学界的一致批评呢?考虑到时代风气、创作语境等因素,笔者认为,一个直接原因应追溯到清中期以降,“摇摇摆摆”一词适用范围的缩减。
具体而言,“摇摇摆摆”在褒贬色彩、修饰对象上,越来越倾向于贬义,其讽刺意味愈加浓厚。
以成书略晚于《红楼梦》的小说《歧路灯》为例,据笔者统计,在上海图书馆藏钞本《歧路灯》中,“摇摇摆摆”一词共出现6次,其修饰对象分别为:市井无赖夏逢若(3次)、俗吏钱万里(2次)、败家子弟张绳祖和王紫泥(1次)。64小说中,没有一位正人君子、大家闺秀以“摇摇摆摆”的姿态出现。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
晚清以降,在小说中“摇摇摆摆”出现的,几乎很少有正面人物。

《海上花列传》第六十四回描写赵朴斋“摇摇摆摆自北而南……较诸往昔体面许多”65;《官场现行记》第十九回描写不学无术的刘大侉子、黃三溜子被署院讥讽后“方才摇摇摆摆的退了下来”66、第三十五回描写何师爷自抬身价“从此摇摇摆摆,每逢官场有事,他竟充作大人大物了”67;《海上活地狱》第三十回描写金生“摇摇摆摆,出入于大赌场中”68;《九尾龟》第三十一回描写赛飞珠出场:“秋谷忽见一个滑头滑脑的人……摇摇摆摆的晃了过来”,更有甚者,书中“有名荡妇”“林黛玉”,在和邱八口角后,“摇摇摆摆的一直往外就走”69。
可想而知,这一时期的读者面对《红楼梦》程本中“摇摇摆摆”的林黛玉,会产生何种联想。这是特定词汇的适用范围发生细微变化造成的独特现象。
因此,在清中期的“修改者”及评点者眼中通俗常见的“摇摇摆摆”,在民国读者眼中“即成恶礼”、“唐突潇湘”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正如民国时期《古今小说评林》所录太冷生(刘铁冷)之评论:“醉心《红楼梦》者,往往寻疤觅疵,挑剔书中情节,亘二百年而未有已。”70在描写对象为林黛玉的情况下,相关文字更易受到读者的特别重视,“摇摇摆摆”一词亦是如此。
从校勘角度看,从“摇摇”到“摇摇摆摆”,只是《红楼梦》传世文本中文字变动的一例,在古代小说的流播过程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。

但是,从文本的流传与接受角度,这一例证充分体现出不同的文本修辞,在不同的时代呈现的迥异的文学效果;同时,对异文的择取和校勘,亦体现出不同时代读者的审美倾向,这对于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流传与接受而言,不失为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实例。
注释
①、23、24、61 曹雪芹、高鹗《红楼梦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122、68、66、1553页。
②胡适《红楼梦考证》,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,第88页。
③曹雪芹著、脂砚斋评《原本红楼梦》卷一,民国九年(1920)石印本(有正书局小字本)。
④俞平伯《红楼梦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,第205页。
⑤邹光椿《红楼梦华》,载《邹光椿文集·第11集》,时代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,第275页。
⑤王漫宇《汉语修辞艺术谈》,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,第17页。
⑦周中明《“只有一个词可以表现它”——论〈红楼梦〉语言的准确性》,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第11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,第212页。
⑧、51 何满子《画虎十年》,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,第139页。
⑨格非《文学的邀约》,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107页。
⑩梁归智《红楼探佚红》,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,第105页。
⑪、45 胡文彬《感悟红楼》,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,第141、142页。
⑫黄龙《红楼梦涉外新考》,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,第109页。
⑬高洪兴《缠足史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,第87页。
⑭曹雪芹、高鹗著,东观主人评《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本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,第287页。
⑮⑯冯其庸纂校订定、陈其欣助纂《八家评批红楼梦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,第199、199页。
⑰苗怀明主编《王伯沆批校〈红楼梦〉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153页。
⑱苗怀明《王伯沆和他的〈红楼梦〉批校》,载苗怀明主编《王伯沆批校〈红楼梦〉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序言第7、14页。
⑳毛公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正义《毛诗正义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,第146页。
21、司马迁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2261页。
22、长白浩歌子著、冯伟民校点《萤窗异草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208、299页。
25、曹雪芹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:甲戌本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235页。
26、曹雪芹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:己卯本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175页。
27、谢翱《晞发集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188册,第296页。
28、杨亿《西崑酬唱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,第123页。
29、曹烨《曹司马集》,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111册,影印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,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,第958页。
30、高士奇《归田集》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·第九辑》第16册,影印清康熙刻本,第743页。
31、杜牧《樊川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,第66页。
32、温庭筠著、曾益等笺注《温飞卿诗集笺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第62页。
33、36、陆游著、钱仲联校注《剑南诗稿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,第2773、2832页。
34、樊增祥《樊山集》卷十一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762册,影印清光绪十九年渭南县署刻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,第279页。
35、白居易著、朱金城笺校《白居易集笺校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,第660页。
37、郭茂倩编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《乐府诗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第867页。
38、元好问著、施国祁注《元遗山诗集笺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,第204页。
39、葛鸦儿《会仙诗》,《全唐诗》卷八百一,中华书局1960年版,第9014页。
40、张祜《张承吉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,第32页。
41、欧阳修《欧阳修集编年笺注》,巴蜀书社2007年版,第531页。
42、曾枣庄,吴洪泽编《宋代诗赋全编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2677页。
43、李昉等编《太平广记》,中华书局1961年版,第3996页。
44、洪迈撰、何卓点校《夷坚志》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29页。
46、48、53、58、施耐庵《水浒传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,第312、971、804、594页。
47、吴承恩《西游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,第151页。
49、52、59、凌濛初著,陈迩冬、郭隽杰校注《拍案惊奇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108、115、303页。
50、冯惟敏《海浮山堂词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,第94页。
54、罗懋登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,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,第371-383页。
55、60、凌濛初著,陈迩冬、郭隽杰校注《二刻拍案惊奇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,第498、500页。
56、梦觉道人、西湖浪子辑,张荣起整理《三刻拍案惊奇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,第262页。
57、陈端生《再生缘》,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,第1067页。
62、秦子忱撰著、乐天标点《续红楼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,第68、149页。
63、华广生《白雪遗音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26页。
64、李海观《歧路灯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,第119、120、703、890、940、1269页。
65、韩邦庆著、典耀整理《海上花列传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545页。
66、67、李宝嘉《官场现行记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,第321、605页。
68、雷珠生《海上活地狱》,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,第188页。
69、张春帆著,唐世明标点《九尾龟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,第171、136页。
70、朱一玄主编《红楼梦资料汇编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,第895页。
东南配资-东南配资官网-配资入门炒股-股票配资平台网址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